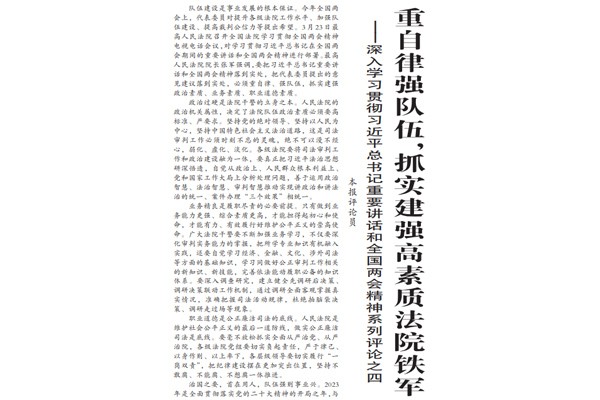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天玉
在我国劳动用工实践中,建筑工程、物流运输、家政服务等领域长期存在多层转包、分包、挂靠经营等非规范用工模式。此类用工模式虽在特定历史阶段促进了市场活力,却因其主体资格瑕疵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失灵。当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下统称实际用工主体)通过承包、分包或挂靠方式介入用工链条时,劳动者在遭遇欠薪、工伤等权益侵害时,常因责任主体缺失陷入维权困境。转包现象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筑市场放开后形成的“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多层结构,法律虽明令禁止无资质主体承接工程,但实践中的“内部承包”“合作施工”“劳务外包”等名目不断翻新,致使真正招用劳动者的实际用工主体大多游离于监管之外。挂靠则表现为不具备资质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支付固定“管理费”取得具备资质企业的名义与许可,从而进入受准入限制的行业。二者的共同特点是“用工外观”与“用工实际”发生分离:劳动者往往穿着被挂靠单位的工作服、使用承包项目部的门禁卡,却因用工主体资格及劳动关系合意的障碍,要求承包人、被挂靠人承担责任存在难题。
既往司法裁判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存在分歧,可归纳为三类路径:第一,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认为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主体之间仅成立劳务或承揽关系,并因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主体的前一手合法单位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而否定存在劳动关系,亦否定承包人或被挂靠单位的用工责任;其二,以“事实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穿透多层合同确认劳动者与具备资质的合法主体成立劳动关系,但裁判说理负担较重且标准不一,在基层司法实践中适用比例有限;其三,采取侵权归责方法,援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或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令承包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执行顺位上劣后于直接责任人,效果有限。上述分歧可能会造成“同案不同判”,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障、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和第二条,确立“承包人的用工主体责任”和“被挂靠单位的用工主体责任”两项重要规则。第一条将“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承包人”作为责任锚点,超越传统控制理论,不再聚焦其是否直接行使指挥监督权,只要存在向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体的转包或分包,即可构成法定的用工主体责任。该用工主体责任范围涵盖工资、加班费等劳动报酬及工伤保险待遇。第二条则以“被挂靠单位”为责任主体,其归责基础并非仅仅依据挂靠协议的证明效力,还在于被挂靠单位通过出借名义、账户、印章等事实上的挂靠行为,确认该情形下产生了“用工单位形式”的合理信赖,故要求其承担与前述第一条中承包人同等的用工主体责任。两条款发展了我国劳动争议司法实践和劳动政策所确认的“用工主体责任”,独立于“劳动关系下的用人单位责任”,将“用工主体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不以合意为前提的公法化责任,统一了司法裁判尺度。
在规则构造层面,两条款引入的“用工主体责任”体现了承包人、被挂靠人承担责任并不以“规避法律”或“损害劳动者”为主观要件,而是直接以“资质缺失﹢劳动者权益受损”为客观触发条件,降低了劳动者的举证难度。同时,用工主体责任的范围限定在工资与工伤保险待遇等核心权益,避免了扩张至经济补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等劳动关系项下请求权,体现出司法裁判规则的克制立场与比例原则。
在规则适用层面,法院应建立递次审查框架:第一步,审查承包人或被挂靠人是否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第二步,在承包人或被挂靠人资质齐备的前提下,审查是否存在转包、分包或挂靠事实,综合考察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施工现场管理权的实际归属、工程款或业务款的资金流向、劳动者受领指令之来源等证据要点;第三步,确认劳动者是由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实际用工主体直接招用,并遭受工资或工伤损害,且用工行为是转包、分包、挂靠业务的组成部分;第四步,确定责任范围,工资计算依据劳动者在实际用工主体处给付劳务的完整期间,工伤待遇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的待遇标准。
综上,第一条和第二条两个条款赋予“用工主体责任”新的内涵,将“用工外观”与“资质控制”明确为责任基础,完成了从“合同相对性”向“规定强制性”的跨越,在劳动权益司法保障层面则实现了“防范用工风险外溢”与“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双重目标,将在灵活多变的经济现实中持续发挥积极的规范效果。